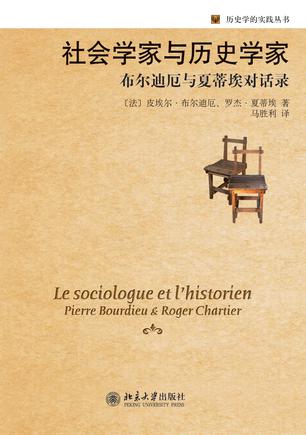《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马胜利译)一书出版
这是一本小书,但它涉及的却是两位大家对两个重要学科的解释和看法。1988年,应法国文化电台《名人直白》栏目之邀,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与著名历史学家罗杰•夏蒂埃进行了5次对话。本书便是这一系列对话的完整记录。
布尔迪厄(1930-2002)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1968年起任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社会学部主任,1982年起任法兰西学院社会学教授。他著述颇丰,多达340余种,涉及人类、社会学、教育、历史、政治、哲学、美学、文学、语言学等领域,其中主要有《阿尔及利亚的社会学》、《实践理论概要》、《再生产》、《背井离乡》、《区隔》、《学术人》、《艺术法则》。国际社会学协会将《区隔》一书评为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学著作之一。布尔迪厄的理论和学术观点在欧美知识界颇具影响。在社会学研究方面,布尔迪厄开创了许多调查架构和术语,如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以及习性、场域、符号暴力等概念,用以揭示在社会生活中的动态权力关系。场域理论是布尔迪厄社会学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他提出,场域中充满着力量和竞争,个体可选择不同的竞争策略,资本既是竞争的目的,又是竞争的手段;场域有自主化的趋势,但场域本身的自主性又受到外来因素的限制。习性是与场域相对应的一个基本概念,习性与场域紧密结合。布迪厄通过场域理论,为实践自己的社会学宗旨,为超越主客观二元对立,做出了较为成功的尝试。另外,布尔迪厄还继承了以佐拉和萨特为代表的法国知识分子传统,他的著作经常持批判西方哲学的传统立场。他积极投身社会活动,批判阶级社会,并因此招来不少非议。英国卫报评价他是可与福柯、巴特等人齐名的思想家。
夏蒂埃(1945-)毕业于法国高等师范学院,1970年起任教于巴黎第一大学,1978年起任教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2006年出任法兰西学院“现代欧洲的写作与文化”客座教授。他以文化史研究著称,其著作有《法国出版史》、《法国大革命的文化根源》、《阅读实践》、《西方世界的阅读史》等,并于1992年获得法兰西科学院大奖。夏蒂埃被学术界归为“第四代年鉴派史学家”,但其治史观念与前一代年鉴学派已有很大区别。他研究视野宽阔,突破了法国自成一系的史学传统,善于结合当代西方史学前沿,尤其是英美新文化史研究的潮流,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新文化史观。他对年鉴学派的时段论、“系列史”、心态史等概念有所批判,认为文化既不是传统思想史所描述的知识精英的专利,也不是心态史中从属于“短时段”历史经验的一部分,更不是仅用量化就可归纳的轮廓或趋势。在著书立说的同时,夏蒂埃还借助大众传媒开展学术普及活动,他在法国文化电台主持“星期一史学”、“名人直白”等栏目在学术界和公众中有很大影响。
要深入理解两位著名学者的上述对话,还应对1988年的学术背景有所了解。众所周知,法国的历史学和社会学是两门颇具影响和地位显赫的社会学科。然而,它们之间的关系却并不融洽,历史学界和社会学界的相互冲突和交锋时有发生。上世纪70-80年代在法国学术界占主导地位年鉴学派偏重“长时段”历史,更鄙视社会学只关注“不牢靠和不可捉摸的现实”。因此,布尔迪厄的《区隔》一书出版后便遭到众多历史学家的抨击。而以布尔迪厄为代表的社会学家则批评法国的历史学家远离现实,只注重“死亡的和埋入地下的东西”。但另一方面,80年代末的年鉴学派已开始呈现危机。吉拉尔•努瓦里埃尔、弗朗索瓦•多斯和罗杰•夏蒂埃等历史学家对法国历史学的状况和年鉴学派的传统理论提出了怀疑,他们同时还试图借鉴其他社会学科的方法和理论来纠正年鉴学派存在的问题。布尔迪厄与夏蒂埃的对话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因此,从《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的书名中,我们既可以感到这是两个学科之间的交锋,又可以看到它们相互沟通和理解的愿望。
本书收录的5场对话分别以社会学家的职业、幻觉与知识、结构与个人、习性与场域,以及马奈、福楼拜和米什莱为题,它们涉及了布尔迪厄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在交流中,两位学者并不回避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但却都能相互倾听对方。夏蒂埃通过提问和插话,尽量让布尔迪厄表明其社会学的重要理念和内心思考,并努力从中发现社会学与历史学的相通之处。布尔迪厄也抛弃了往常的激烈言辞,力求平心静气地解释自己的看法和感受。他甚至多次对夏蒂埃的观点表示肯定和赞同。与激烈的学术论战不同,这种平和态度和沟通气氛有助于人们看清法国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和深刻理解布尔迪厄的重要理论、观念和思考。
20多年后,即2010年,法国“阿高纳”(Agone)出版社决定将上述系列对话作为小册子全文发表。它认为,这组对话不仅能够告诉人们众多学界事实,还会启发读者思考。而且,该书的对话形式显得生动活泼,令人读来轻松舒畅,有助于让一般读者了解法国的社会科学状况和布尔迪厄的复杂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