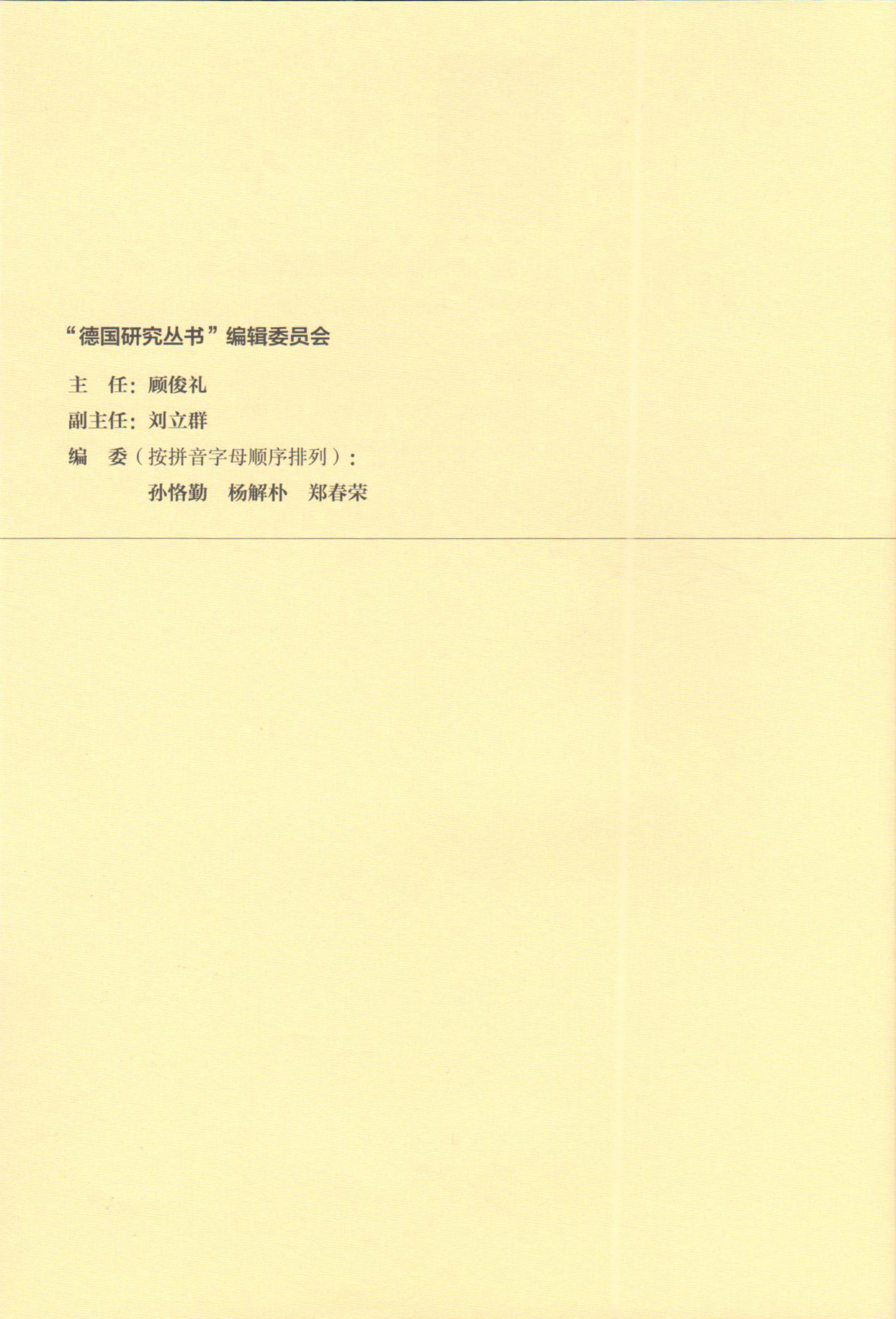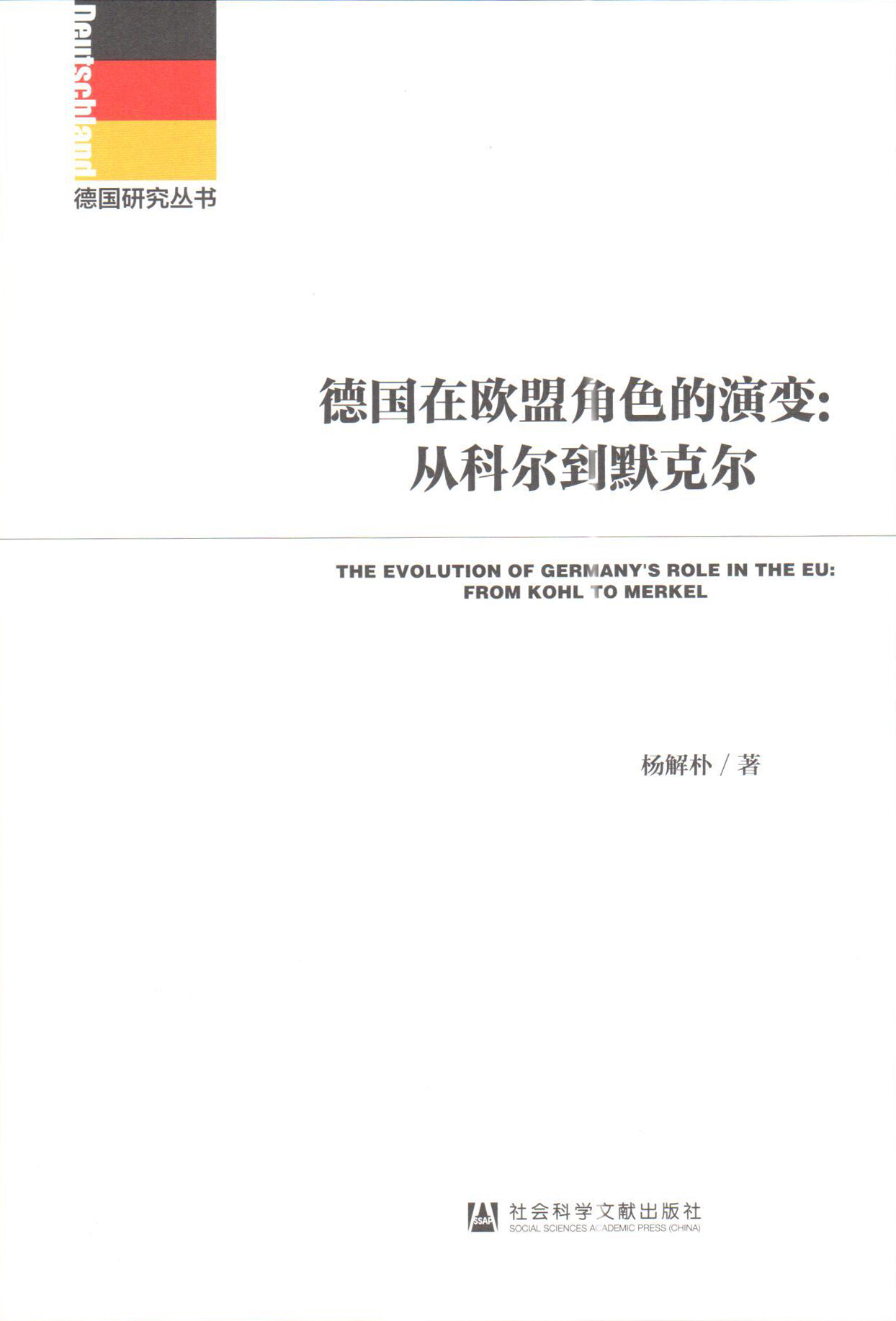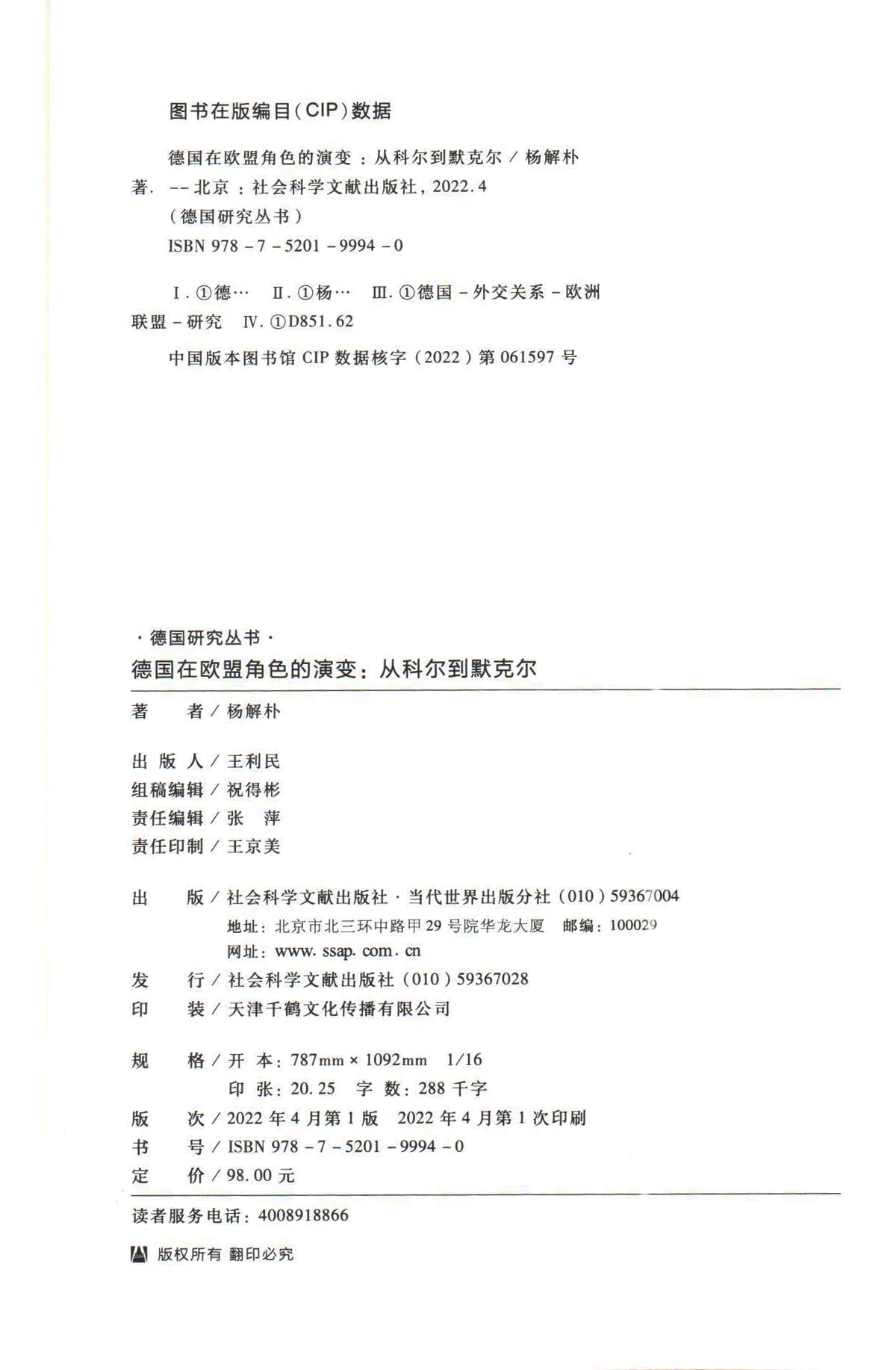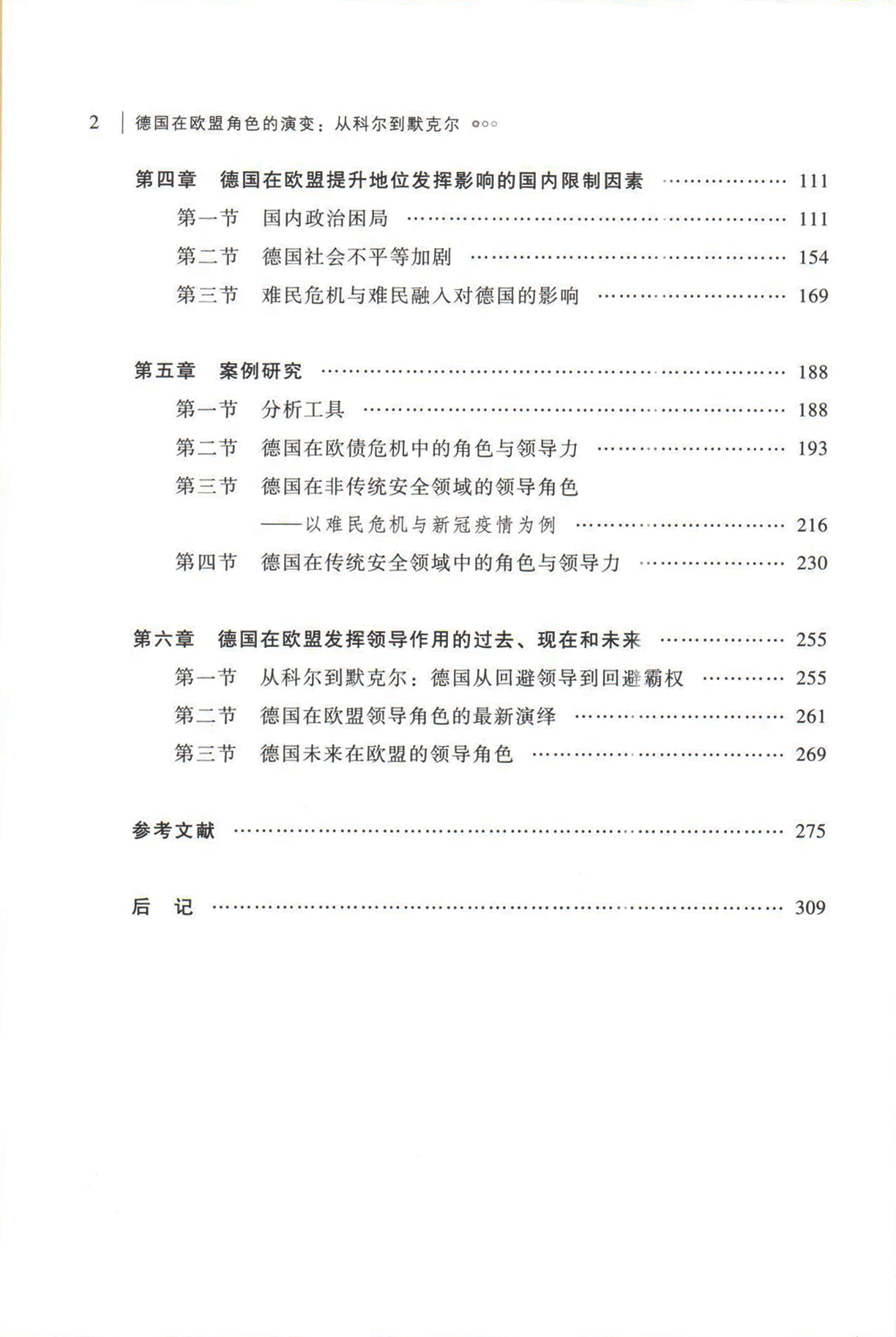杨解朴:《德国在欧盟角色的演变:从科尔到默克尔》
导言
在欧洲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德国在欧盟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两德统一之前,德国虽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但在欧洲政治舞台的影响力与其经济地位并不匹配。两德统一之初,德国也并未谋求在欧洲事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彼时德国首先要解决的是统一所带来的沉重的财政负担问题,以及东部和西部社会制度融合过程中所面临的各方面的困难。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由于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不断攀升,德国还曾被称作“欧洲病夫”。但是,在两德统一30年后,德国在欧洲乃至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德国在欧盟的实力和地位不断提升,特别是在欧债危机的解决过程中,凭借其经济实力,德国在欧洲的领导地位凸显。在乌克兰危机的处理中,德国在欧洲外交安全领域表现出积极有为的态度,成为解决这一危机的欧洲一号领导者。有学者将德国称为“不情愿的霸权”,也有学者认为德国实现了“重新崛起”,但面对愈演愈烈的难民危机,欧盟层面始终拿不出有效的解决办法,德国的难民政策面临多重困境。在难民危机的处理上,德国基本无法改变其他欧盟国家的意愿。难民危机甚至还引发了恢复成员国边境控制的提议,使欧洲联合面临倒退的风险。与此同时,欧洲团结面临考验,英国退出欧洲联盟,欧盟国家“脱欧”“疑欧”的倾向有所增强。在新冠疫情后经济复苏的政策协调中,德国做出了巨大妥协,为欧盟疫后经济复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到底该如何评价两德统一以来德国地位和作用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德国在欧盟的地位和作用又受哪些因素的推动和制约?如何定位德国在未来欧盟中的作用?德国地位和作用的变化,给其外交政策乃至中德关系和中欧关系带来哪些影响?我们将带着这些问题开始本课题的研究。
两德统一以来,随着德国实力的增强,国内外学者对德国应如何发挥其在欧盟和国际上的作用给予了充分关注,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分析了德国道路的问题。
两德统一后的20世纪90年代初,德国的外交政策专家、学者以“正常化”为前提,讨论德国应该如何像其他欧洲大国一样“正常”地制定和推行其外交政策。“正常化”的主张者强调,德国重新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后,应该有自己的外交政策利益和目标,同时将相应地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持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冈瑟·赫尔曼(Gunther Hellmann)认为,冷战结束和两德统一后的欧洲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德国国力明显增强的同时,新的问题也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不断出现,德国应承担更多的责任,这就迫使德国放弃由于东西方冲突和历史原因而使用军事手段采取的限制。另一位典型代表埃贡·巴尔(Egon Bahr)认为,德国应该像其他大国一样在国际事务中“正常”地发挥作用。德国不应该像某些美国批评者所说的那样继续成为美国的附庸,在重大问题上德国应该有自己独立的主张。德国应该重新具有“大国意识”,但不可骄傲自大;德国乃至欧洲与美国的关系应由过去那种“舒适的监护关系”转变为一种“成熟的伙伴关系”。但也有欧洲学者反复强调,德国提出和实行“正常化”外交政策时不应过高估计自己的实力,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德国的利益在统一后同样需要通过与其他国家协调和合作才能实现。以汉斯·W·毛尔(Hanns W. Maull)教授为代表的角色分析派从国家角色期待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关于德国作为“文明力量”的国家角色的论点,强调承担这一角色的国家应当从整体上对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进行考量,主要采用“文明力量”手段来追求国际关系文明化的目标。沃尔克·里特贝格尔(Volker Rittberger)则以“权力国家”、“贸易国家”和“文明国家”三种模式验证统一后德国外交政策的连续性。
伴随着国际秩序的变化和欧债危机的爆发,德国在欧盟的实力和政治影响力不断增强,有西方学者认为,德国外交政策更多是践行“正常国家论”的道路,他们在讨论新德国外交政策的同时,开始讨论德国是否已经成为欧洲的领导者乃至扮演霸权的角色。例如,2013年《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杂志的一篇评论文章将德国称为“不情愿的霸权”,认为正像战后美国担负起领导职责援助当时脆弱的西德一样,现在该轮到德国领导那些深陷危机的盟友了,这既是为了盟友,也是为了德国自身的利益。伴随着难民危机、乌克兰危机的发生,西方学者又热衷于研究德国的领导作用及其限制因素。利斯贝斯·阿格斯塔姆(Lisbeth Aggestam)等人用角色理论以乌克兰危机为例分析了德国在欧洲外交安全政策中的领导角色;西蒙·布尔默(Simon Bulmer)和威廉·E·帕特森(William E. Paterson)以欧债危机、难民危机和乌克兰危机为案例探讨了德国是否能在欧盟充当霸主的问题,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德国仅是“欧盟经济霸权的候选者”,并指出阻碍德国成为欧洲霸主不仅存在各种国内限制因素,还包括欧盟的制度性限制因素。
甘瑟·迈霍尔德(Günther Maihold)认为,伴随着德国国内政治的发展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德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越发不能用静态的类别来把握,它受到政治碎片化和相关行为者格局的影响,确定基本方向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国家间和国际上的协调需求不断增加;汉斯·W·毛尔用角色理论分析了德国外交政策该如何适应来自右翼民粹主义的挑战和来自合作伙伴的新期望和要求。
伴随着新兴国家的兴起,德国在世界中的定位以及德国如何作为欧洲的代表与这些国家发展关系也成为西方学者热议的话题。丹尼尔·弗莱姆斯(Daniel Flemes)等人认为,德国的外交政策正日益从传统的基于价值的伙伴关系转向以利益为基础参与不断变化的联盟和网络,德国在处理与西方价值观和标准存在差异的国家(如中国、土耳其、哈萨克斯坦)的利益关系时面临两难困境,并面临着失去作为国际调解人的信誉风险。但如果德国想在国际危机中扮演可信的欧洲“首席调停者”角色,以利益为导向的网络外交也应该始终支持以价值为基础的原则。罗伯特·卡佩尔(Robert Kappel)等人探讨了随着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德国应如何在一个新的世界中定位自己的问题。马可·西迪(Marco Siddi)认为,德国在欧盟与俄罗斯关系中长期寻求领导地位,德国不是一个“不情愿”的国家,而是一个在这一政策领域独断专行的霸权国家。
中国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对统一德国实力和地位的变化及德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和连续性进行了跟踪性研究和理论探讨。进入21世纪,中国学者继续探讨德国地位的变化和发展道路,特别是将“德国问题”、“新德国问题”以及“德国问题”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作为热门选题。同时,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不断拓宽,开始研究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来回摇摆的原因、德国对欧政策以及德国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的立场。
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爆发后,对于德国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中国学者一方面聚焦到德国模式以及德国模式是否适用于其他国家的讨论上,另一方面又重新展开了对“德国问题”、“新德国问题”以及“德国的欧洲”和“欧洲的德国”的讨论。在乌克兰危机的解决中,中国学者也关注到了德国外交政策的转变;在难民危机的协调中,学者们梳理并总结了德国在难民危机中的政策调整、困境、原因及影响,同时探讨了难民给德国乃至欧洲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新冠疫情背景下,中国学者分析了德国在新冠疫情中的应对措施及新冠疫情对德国政治、经济和外交的影响,并对德国在新冠疫情中在欧盟的领导角色予以关注。近年来,中国学者对数十年来德国在欧盟乃至国际事务中的角色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有学者认为,德国在半个多世纪中践行了嵌入式崛起,在大国地位稳步上升的同时,避免了与现有霸权国及其体系之间的紧张关系。但德国的嵌入式崛起使其在国际安全领域追求大国地位时遭遇了困境,即在由实力政治主导的现有国际安全秩序中,德国试图推行以规范代替实力的全球安全秩序观,不但有悖于主导国所推行的全球安全秩序并对其构成挑战,而且面临着嵌入与崛起之间的两难。有学者认为,近年来德国在欧盟的领导作用呈现明显弱化的趋势,这一趋势与内政困局、社会生态的变化及经济结构性缺陷等内部因素和欧盟成员国利益分化、全球大国博弈加剧等外部因素有关,并将加剧欧盟成员国对立,制约欧洲一体化进程,也使欧盟在全球的地位进一步受挫。有学者从国际关系研究的变量出发,分析了六个层次的变量所形成的合力导致德国红绿联合政府外交面临的不同的平衡挑战,在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中,红绿政府的外交形成了“克制文化”与“责任文化”交织共生的特点。有学者以“文明力量”理论为分析框架,分析了受文明力量影响的德国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及德国的国际角色,将文明力量作为德国建构新兴国际关系体系的理论工具。中国学者在研究德国地位和作用的同时也心怀对中国的关切,他们探讨了德国在中欧关系、中欧光伏争端中的作用等。
本研究将以两德统一以来德国在欧盟的地位和作用为研究对象,与现有的其他研究成果相比,本研究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笔者对德国统一30年来的对欧政策以及在欧盟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进行系统的、综合的、跨学科的研究。从上述对学术史的梳理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就德国地位的特殊性、某一时间点德国外交政策转型所做的研究较多,但对于德国统一以来在欧盟地位和作用动态变化的系统性研究尚不多见。第二,笔者以目前欧洲一体化遭遇的问题和挑战以及德国国内的制衡因素为基础,尝试预测在未来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德国的地位和作用。